这部以精神病患者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《囚》,让那些病灶各异的精神病患者,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,说出了隐晦而私密的往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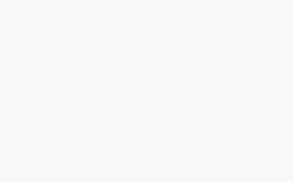
长春六院,精神病患者看向窗外。展映组织方供图
文|实习生 王双兴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
编辑|苏晓明
本文全文共3216字,阅读全文约需6.5分钟
►窗边的中年人以一副置身事外的语气说:“砍了三十多刀。幻听,外面进来两个人,说我不杀了她,他俩就杀了我。”于是他砍了自己的媳妇。
睡不着的少年起身又躺下,用力地闭眼、打哈欠,对普通人而言最简单的“睡觉”,换成他,反倒像在安慰守在一旁的母亲。
背对镜头的男子伸手去开被牢牢锁住的窗,一扇打不开就去打第二扇,从左到右,四扇窗逐一尝试个遍,窗户纹丝不动。
这些举止不寻常的人是长春六院(长春市心理医院)的患者,也是导演马莉镜头下的主角。
3月18日,这部以精神病患者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《囚》,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小展厅里点映,年轻的观影群体给出了笑声、掌声、啜泣声以及大段的沉默。
一个多月前,片子在柏林电影节首次“登台亮相”,面前是不同肤色、不同国别的观众,身后是“入围第67届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”的殊荣。
作为柏林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,论坛单元侧重选择那些来自不同视角、独立于电影体制传统、对当前社会保持敏锐观察且具备艺术创新的片子。
马莉把镜头对准了精神病患者,用近乎黑白的低饱和色彩,呈现他们不被理解又无法挣脱,难以回到正常生活的困境。
“被‘囚’住的人”
裸露红砖和水泥的墙壁的展厅里,很多人用几个小时的车程赶来,来看这部比乘车时间还长的纪录片。
一百人左右的放映厅内,人已经坐到了两侧的石阶上,有人被挤到了门口。
灯光暗下,荧幕上一段俯拍的监控录像出现,一个病人在病房中反复踱步。平稳无声的画面,只有左下角的时间码快速变动,硬生生地把“时间”的概念抛了出来。画面突然消失,嘈杂声乍起,观众被“抓”进了长春六院(长春市心理医院)的重症封闭区。
在这里,有人狂躁地哭泣、叫喊、搬床;有人则僵硬地躺在病床上,目光如炬。几种极端的情状在狭小的空间同时出现,重复上演,精神病患者的困顿与挣扎,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单人作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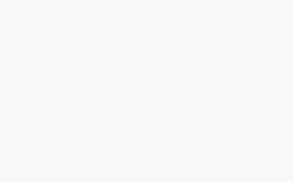
导演马莉。
这场“战争”以纪录片的形式持续了287分钟,落幕之前,患病的大学生渐渐有了笑的能力。他非常“清醒”地与病友争锋——
“啥是吃饭?我想不起来啊。”
“做好饭就吃呗。”
“啥是吃?我想不起来。”
“张嘴吃呗。”
“你叫我张嘴我能张嘴,那吃咋办?你叫我往里塞我能做到,那是咽还是吃我也不知道啊……”
他陷入一个自我设置的命题里,通向“正常”的牢笼打不破,去往“清醒”的问题想不通,像个被“囚”住的人,无法突破自己的困境。
这正是马莉想要呈现的精神病患者现状,黑白的色调在影片里徐徐展开,在点映现场,她说,“这更接近我心理上的真实(色彩)”。
这位197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女导演,在2010年创作了《无镜》,在2011年完成了《京生》,之后的5年,又到精神病医院进行长期拍摄,有了第三部作品:《囚》。
倾听与信任
马莉对人性和困境有特别的兴趣,“我总是觉得人很脆弱,但也很坚韧,在困顿当中有一些非常非常闪亮的东西。”在拍摄这三部曲之前,她拍了大概几十部人物传记。
和以前一样,马莉一个人完成了《囚》的导演、拍摄和后期处理。最终在长达15000分钟的素材中,选择了287分钟呈现到了荧幕上。
拍摄过程中,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,马莉待在封闭疗区,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。她对媒体说,不希望自己开始的是“一场掠夺性的拍摄”。
真实呈现是马莉的拍摄初衷,她选择了以寻常的心态进入,“带不出新片也没关系”。
那三个月里,她住在医院,和他们共同生活,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来相处,并不停地阐述自己进入病区的用意,“也希望他们明白,他们有拒绝拍摄的权利”。
前期花下的功夫最终通过影片中的诸多细节展现出来。那些病灶各异的精神病患者,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,不在意机器的存在,他们暴戾和抓狂,自言自语,会纠缠于自己提出的“重大命题”,也会哽咽、说出些隐晦而私密的往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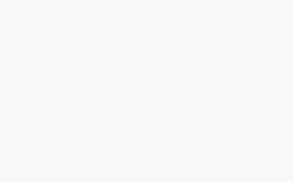
长春六院,护士坐在走廊里值班。
倍感医院压抑的男人歪着脑袋问:“你说马莉我是不是得跑?”
永远忧心忡忡的创业者对着镜头说:“昨天我生日,蛋糕忘了给你留了。”
不承认往可乐里兑药的吸毒者信誓旦旦地告诉护士:“你问马莉,她看到了。”
但马莉始终站在镜头之外,无所回应。“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内心,让他们自己来传达这种感觉。”所以她选择和观众站在一起,只负责倾听。
这种毫无打扰的倾听,去除了同情和凄迷,让患者自己走到舞台正中,沉默者自然开口, 到达了“导演被拍摄主体信任,片子值得被观众信任”的效果。
“根本不是精神病,这是死亡的真实体验”
很少有什么病症是凭空而来,精神病也一样。
马莉的纪录片,让观众关注到了精神病患者内心挣扎之外的外在困境。
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,经历过父母离异,经历过抢劫犯罪,在少管所里被灌了铁砂的管子削(打),精神崩溃,患上了抑郁症。
他说,“根本不是精神病,我这是死亡的一种真实体验。”
突然而来的哽咽,他用读诗的语气,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们不了解单亲家庭的孩子,没人理解他,没人开导他,如果有人带带,都是好样儿的,都是孝子贤孙。”
“小伙子你为何这样忧愁,为何低下了你的头……”病友的歌声响起,很少可以洞悉拍摄者情绪的纪录片,被这个小小的蒙太奇,透露出导演的悲悯。
除此之外,创业后的躁狂者,离婚后崩溃者,吸毒失控者,酗酒犯罪者……特征十足的时代,变动的社会,复杂的人性,借助精神病患者铺陈开来。
他们从那样的环境中来,接受治疗、疏导,是否还将回到那样的环境中去?
马莉的纪录片没有给出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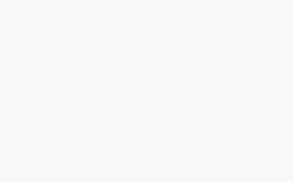
一位躁狂症患者站在窗前。
2013年,是《囚》的拍摄后期。那一年的5月1日起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正式实施。精神卫生法规定: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。
展映结束后的互动环节,这项规定被观众拎出来探讨。如果不是拍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,马莉或许永远不会接触这样的一部法令。
但拍出了《囚》的她,对原本和工作生活毫不相干的事物有了自己的理解:实际上这个法案对他们来说影响不大,病人可以提出出院,但却做不到出院后正常生活。来自个人、家庭、社会的各方压力,都可能让他们倍感艰难。
“有时候可能你的一个异样的眼神,都让他无比难受。”在点映现场,马莉顿了顿,“我希望你们能够因为这个片子,对他们有些不同。”
“无人能解的困境”
不止一位观众说,《囚》的观影体验是复杂的。
东北人的语言天赋,常常让人忍俊不禁。长春六院里的病患,一本正经爆出的金句惹来笑声,有时说出一句正常人想说但没胆儿说的话引起掌声,转而又被无处不在的压抑带来漫长的沉默,抽纸巾的声音都能被听到。
有人看完片子写短评,提到观影的某个瞬间,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神经病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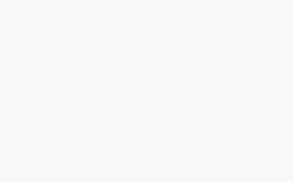
一位患者在病房里读书:《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》。
片子里,一个爱写诗的老人提到他当国民党特务的父亲,老爹被枪毙,他的童年都是“抬不起头”的经历。几十年后,曾经的“狗崽子”蹲在精神病院的角落里,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着镜头说话。
没人看得懂他前后矛盾的逻辑:一边感慨自己的人生太平常,又紧跟着说了句“活的还挺幸福”;总结自己的一生是混吃等死,又补充一句“人之常情”;“男朋友我都没有,别说女的了”,接下来的却是“生活得还挺愉快”。窗外明月高悬,临回房间,老人嘟囔了一句“同难者相悯”,所以没人可以理解他。
起身,临走,他回过头对马莉说:“你陪我唠这么多嗑,谢谢您。”
他们自言自语,无视身边发生的一切,常常像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人,但却无法真的与这个世界上不发生关联。
当精神病患者出现在恶性事件的新闻里时,这个群体才会搅动舆论场。
马莉说,“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特别地复杂”,与影迷互动时,她的声音始终波澜不惊,但把“特别”二字读得很重。
拍摄《囚》的经历,让她在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困境、救助困境和社会融入困境之外,探知到了他们自身固若金汤的困境——找不到出路解救自己,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,囚禁在一个无人能解的困境中。
“我们遭遇了困境,还可以想尽办法、做出选择,但是他们太无奈了。”马莉说,“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疾病,谁也改变不了,药物只能让他短暂地恢复到清醒的状态,停药很快就会陷入异常当中。这是无法挣脱的,没有比这更让人悲哀的。”
有一位患者卧在床上,手里捧着一本《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》,他说,这是本好书。
片子里,一个留平头的男子不住猜测,“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,我看报纸登的,小布什在月球卖土地,咱们是不是被撵下来了。”